 • 旅行攻略
• 旅行攻略
巴蜀深山中的郪江镇
摄影:王磊
巴蜀土地肥沃宽广,纵横交错地遍布着逶迤的河川。巨江细流沿岸的重峦中,谁也说不清藏有多少汉代的崖墓。对于大多数现代人而言,这些寂静潮湿的洞穴原本无足轻重。亲身走进岩间“室宅”,粲然如初的雕刻却让我如同看见封存的前朝时光。

隐藏于旷野田间的孙家湾崖墓群
摄影:王磊
四川绵阳三台县的郪江古镇位置僻远,游人罕至。石板街头新修的牌坊高悬“郪王城”和“东广汉郡”榜书,追诉着往昔荣耀。事实上,除了地理志的只言片语,山乡地表早已寻觅不到唐以前的记忆。崖墓调查材料陆续刊发后,小镇的名字很快传扬了开来。面对怀揣特殊兴味的访客,乡民们逐渐习以为常。

崖墓墓口的神秘
摄影:陈新宇
东汉以来开凿的崖墓在郪江镇方圆三十里的地界颇为密集。紧靠集镇的金钟山、紫金湾等墓群受到维护,对外开放。更多的墓葬在经过调查和测绘之后,一如既往地荒置在山崖间,被丛杂的草木掩蔽着,很少有人问津。在田野环境下,针对考古遗址的“回访”往往都非易事。

古镇附近的金钟山一区崖墓
摄影:梁鉴
三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入蜀。火车穿越秦岭,循嘉陵江南下,眼前豁然开朗,山河壮阔而润泽。几天之后的清晨,投宿在郪江的我一早就踏出了房门。镇子外,颓败的龙脑桥默然无声,清亮的鸡鸣起伏不绝,群山隐没在乳白色的浓雾里。仗着考古报告的地形简图,我步履匆忙地迈上狭窄的山路,盘算着时间赶往下一组崖墓。

紫金湾一号墓墓壁上的蜀风汉韵
摄影:陈新宇
柏林坡是距离镇子大约六七里的一座矮小山头,坡上坡下共分布了二十多座崖墓,郪江绕着山嘴静静淌过。前一天,探寻被登记为一号墓的大型崖墓未能遂愿;几经歧途,我终于抵达目的地。假若把装饰精美的古代墓葬比喻成幽冥世界的家园,那么与川渝地区多数崖墓组合一样,最阔绰的这座府第位踞中央。墓口并不显眼,惟有登堂入室,才能发现洞天。

因“狗拿耗子”画像而闻名的金钟山一区一号崖墓
摄影:王磊
低头走进墓道尽头的洞门,木结构建筑的形象毫不意外地扑面而来,让人应接难暇。甬道径直延伸向山岩内部,两侧的墙壁或者雕梁画栋,或者修凿石室,头顶之上还悬挂着重重藻井。幽黑的崖洞深处,几级石阶通入“寝宅”,正前方硕大的朱红立柱遥相矗立。郪江流域的崖墓常常在尾端设置居于室中的“都柱”,柱子尺度伟然,成为视觉的绝对核心。柏林坡的十六棱圆柱承托方形的栌斗,三面出一跳斗栱,有如伞柄一样擎起了整座后室的屋盖。厝身其间,我的心绪略显激动。平素里只能从画像中窥见一斑的汉代殿堂,眼下竟然触手可得。

赋彩庄重的柏林坡一号崖墓
摄影:梁颂

柏林坡一号墓的后室
摄影:梁鉴
庄子高唱过“方死方生”,苏子低吟着物我无尽。从某种角度看,生与死也许不是硬币的两面。环顾柏林坡一号墓闳阔的后室,参差的柱枋与斗栱玄赤各半,错叠的颜色似乎有意昭示生死的交融。大限固然值得忧戚,营造一座坚固华美的屋舍,大概能够供魂灵永久凭依。徘徊在洞室内,外部世界的声光杳不可及,林林总总的雕刻予人奇妙的幸福感受,几乎忘却今夕何夕。门边轩昂的骏马,梁下栖止的仙鹤,柱头跳跃的猛虎,尽皆带着温度和呼吸,眼前演绎着鲜活的汉朝图景。

吴家湾一号墓的都柱
摄影:梁鉴

柏林坡一号墓的侧室
摄影:梁鉴
巴蜀崖墓绚丽繁华,但是很少留下主人的踪迹,以至于自古以来被误认为“蛮洞”或仙居。有时,惊喜在不经意出现,一号墓的几则题记成为破解建墓人身世的密码。1900年前,时值东汉初平年间,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齐氏家族选择用石刻讲述他们的事迹和情愫。侧室墙壁上绘制着一幅优雅的宴饮图,帷帐高悬,尊盘罗列,夫妇相守而坐。即使肉体终将朽烂,画中身形坚如金石。从前堂转入后室,可以见到一组露骨的连续画面。斗栱之间的空隙里刻出摇曳的男女轮廓,自左向右分别做出私语、牵引和交接的姿态。窥见此景,看客大可不必惊奇:当时的道家认为,房中作乐有助于阴阳调顺,益寿延年,生时不可或缺,来世自然也需照常施行。

绵阳博物馆陈列的东汉崖墓陶俑
摄影:梁鉴
汉代人口口声声呼唤的长生和不朽,借助死后享用的山石厅堂得以实现。墓中一如人间,人丁、资财、酒食、声色,无所不有。躲过盗扰的柏林坡二号墓提供了有关丧葬的更多原始信息。石门揭开后,人们看见逝者葬具的周围整齐地码放着陶俑、陶马,以及屋舍、杯盘等明器。崖墓所见的俑像虽然难逃模范的窠臼,但是足以称得上清新自然。无论窈窕的少女,还是滑稽的俳优,都流露出乐天派的笑靥,谁见了都不禁莞尔。

坟台嘴一号墓的侧室
摄影:王磊

坟台嘴一号墓的“庖厨”
摄影:王磊
从西汉开始,淮泗一带就诞生了横向构造的大型崖洞王陵,中国的墓葬景观由此剧变。川渝崖墓虽不及诸侯王世家的陵墓恢宏雄伟,建造方式却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南边地的东汉豪族因地制宜,利用本地山岩易于扩凿的特点,发明了独特的合葬风俗。宋人在《隶释》中记载,彭山县的一座崖墓总计葬入张氏四代成员。郪江镇规模最大的崖墓位于坟台嘴,院落达到四进,想必也耗费数世之功。

绵阳崖墓出土的东汉陶马
摄影:梁鉴
那些魂归异乡的谪人带着中原的建筑样式与族人宾客一道闯进巴山蜀水。在郪江上游不远处的塔梁子,人们发现一座进深30余米的深邃崖墓,墓中凿出了大大小小十多间龛室。长篇的墨书题记写道,原籍南阳的墓主人拥兵十万之众,前来参加与羌人的鏖战,意欲借此建功赎罪。

坟台嘴一号墓墓门
摄影:王磊
钻出洞口,作别柏林坡前,我习惯性地回望墓门。门楣已经塌毁,看不到石刻的檐瓦。很多时候,门前会刻出一对阙楼,仿佛象征了黄泉的入口。按照计划,我不得不快步向前赶去,等着我的,是躲在苍岩和芜草之间数不尽的时空通道……

紫金湾三号墓的凤阙
摄影:梁鉴
从19世纪末开始,海外旅行家抱着强烈的猎奇心理深入中国腹地,率先对巴蜀崖墓发生兴趣。先后到来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诗人谢阁兰都不信任当地人的说辞,断定这些遗迹应是汉代墓葬。不久以后,战争促使中国的新派学者齐聚西南一隅,对历代崖墓的系统调查渐次展开。截至21世纪初年,考古工作者仅在郪江镇周边就发现了超过千座裸露的崖墓,其中建筑形象丰富的占三百余座。

金钟山二区崖墓的六博画像
摄影:王磊
奢华而又内敛的崖墓建筑在后汉隆盛一时,随后很快趋于式微,渐渐为人们所遗忘。今天的乡人并不计较这些奇怪的洞穴和石室由何人建造,丝毫不以为意地在其中堆满柴草。时近两千年前的“永恒家宅”,终究未能庇佑他们的主人,穿透时光迷雾映射出来的仍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汉代幻象。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艾米时尚网立场。)
 [资讯] 最新一期《阳光姐妹淘》上线啦,本期迎来了人间种草机林允和闺蜜米米做客阳光小屋,一起...
[资讯] 最新一期《阳光姐妹淘》上线啦,本期迎来了人间种草机林允和闺蜜米米做客阳光小屋,一起...
 [资讯] 2021年11月7日,中国,北京——胖虎三里屯旗舰店开业活动盛大举行。开业以时尚蜕变,永续...
[资讯] 2021年11月7日,中国,北京——胖虎三里屯旗舰店开业活动盛大举行。开业以时尚蜕变,永续...
 [资讯] 2013年成立伊始,来自瑞典的时装品牌& Other Stories从位于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洛杉矶三...
[资讯] 2013年成立伊始,来自瑞典的时装品牌& Other Stories从位于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洛杉矶三...
 [资讯] 11月17日,格乐利雅·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登陆上海东方体育中心,ALL IN男团、阿云...
[资讯] 11月17日,格乐利雅·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登陆上海东方体育中心,ALL IN男团、阿云...
 [旅行攻略] 撰文:杨煦摄影:一白
北京二环...
[旅行攻略] 撰文:杨煦摄影:一白
北京二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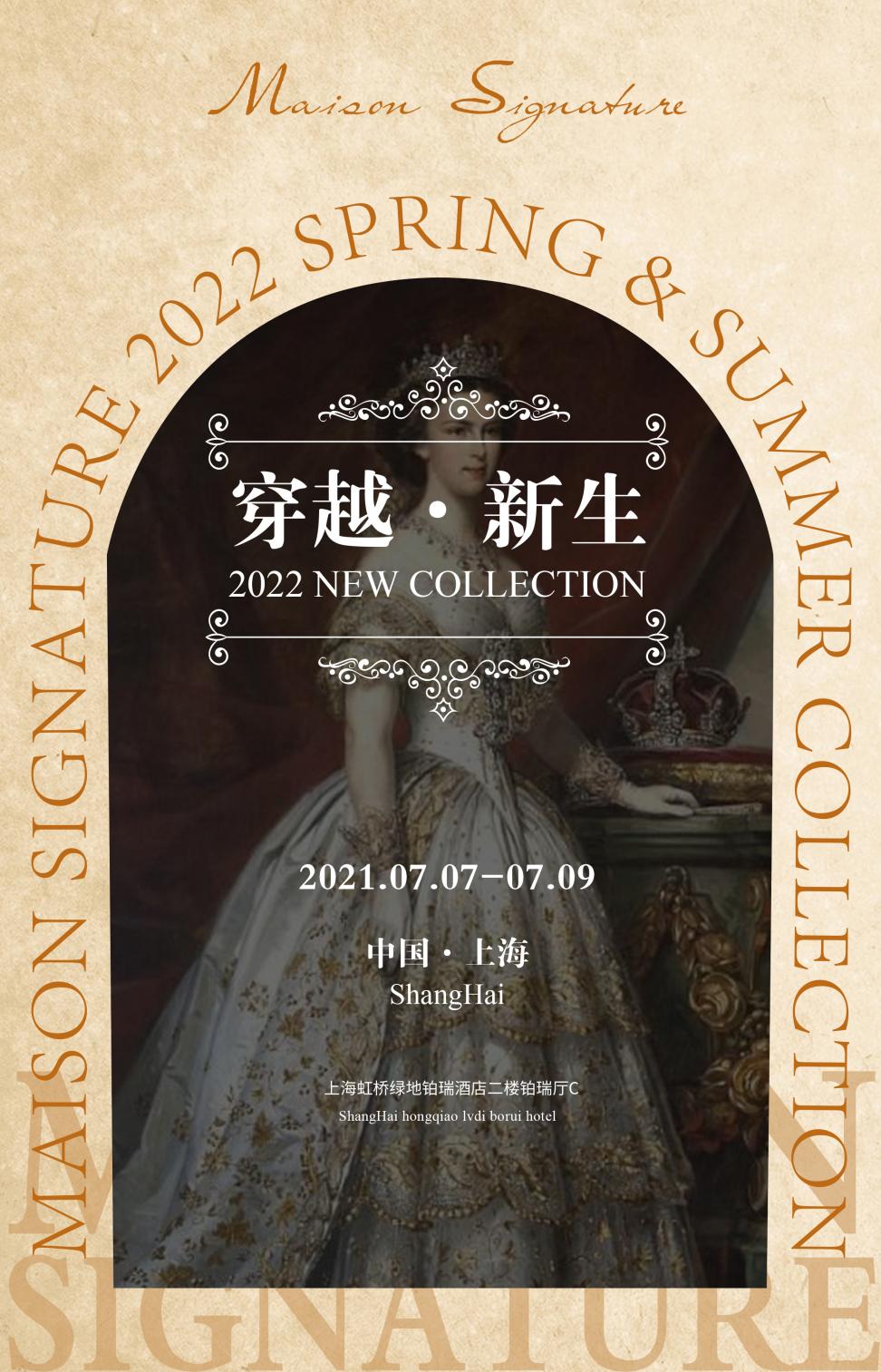 [资讯] 2021年7月7日到9日, 黎巴嫩奢华高定品牌Maison Signature(玫森·赛妮尔)全新高定系...
[资讯] 2021年7月7日到9日, 黎巴嫩奢华高定品牌Maison Signature(玫森·赛妮尔)全新高定系...
 [资讯]2016年8月15日晚间,DAZZLE FASHION携旗下DAZZLE、DIAMOND DAZZLE、d’zzit以及全新推出的...
[资讯]2016年8月15日晚间,DAZZLE FASHION携旗下DAZZLE、DIAMOND DAZZLE、d’zzit以及全新推出的...
 [资讯] 9月6日,知名国产护肤品牌欧诗漫正式官宣火箭少女101组合成员孟美岐成为全新品牌代言人。...
[资讯] 9月6日,知名国产护肤品牌欧诗漫正式官宣火箭少女101组合成员孟美岐成为全新品牌代言人。...
 [新品动态]
导语:
近日,备受好莱坞明星推崇的全球领先医学美容权威品牌Dr Brandt...
[新品动态]
导语:
近日,备受好莱坞明星推崇的全球领先医学美容权威品牌Dr Brandt...
 [搭配]导语:4月13日晚,香奈儿Coco Café限时体验店在上海开幕,品牌好友韩火火应邀出席。火火身...
[搭配]导语:4月13日晚,香奈儿Coco Café限时体验店在上海开幕,品牌好友韩火火应邀出席。火火身...
